1929年12月13日,一场盛大的结婚庆典在旧上海四马路的“一品香大旅社”浪漫上演。有必要介绍一下“一品香”,这家成立于1880年代的旅社,最早的名字叫“一品香番菜馆”,是国人在上海四马路开设西餐馆的始作俑者。它的原址就在现在的来福士广场,和平电影院的旁边。当年的“一品香”就像如今的“新天地”,是沪上备受名流青睐的时尚地标,一楼是西菜馆,承办喜宴能同时容纳几十桌一同用餐,楼上则是旅社客房,共有四五层,非常气派。
这场婚礼的女主人公,是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代总经理的杨敦甫家的女公子,新郎则是杨树浦三新纱厂华尧辉的公子华士润,据说即将从沪江大学附中毕业,婚后将携妻子一同前往日本留学。
关于这场婚礼的细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自己的刊物《海光》月刊一卷第十二期上曾有专文进行过细致而生动的描述。作者应俭甫大约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职员,职位恐怕也不会低。值得一提的是,他似乎在当时的“鸳鸯蝴蝶派”文人间也颇为活跃,是范烟桥、赵眠云、郑逸梅、范君博等人发起的“星社”的雅集常客。这一点,从他风趣盎然的叙事文笔中亦可以得到曲折的证明。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平博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从1929年1月《海光》杂志创刊,直至1949年7月彻底停刊,全部142期《海光》,除却1937年8月号遍寻不着(事实上很有可能因为抗战爆发的关系,这期杂志本身就只有存目而未尝出版),其余各期他都收藏在案。2014年10月,由他编纂的《稀见银行史料初编》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其中,他将手头所掌握的《海光》月刊所刊文稿,以史料学的方式,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分类辑录。听说我们对时期的银行人婚礼感兴趣,刘平又特地将《海光》杂志中谈及银行人婚礼的部分,无论长短大小,一一悉心标出。应俭甫的《华杨婚礼记》便是其中之一。用刘平自己的话说,刚刚拿到银行人婚礼这个题目,他自己都觉得有点犹豫,银行人的婚礼较之普通人难道真的会有区别么?不想一旦投入史料,细读玩会之下,倒还真有意外的感想从中浮出。
回到我们的故事。这场华杨联姻的礼堂设在“一品香”的跳舞厅。婚礼从早上九时一直延续到晚间十时方散,由于男女双方各自的家庭背景,前来贺喜的宾客也多是银行乃至实业界的闻人,从朝至暮,数量竟达四百人之众。一时间,旅社门前车水马龙,蔚为壮观。传说这位低调的杨敦甫先生原本并不打算惊动亲友,所以没有准备喜帖,奈何得到消息前来送礼的人实在太多,人情难却这才赶紧补以请柬,前前后后几次发出的喜帖,光式样就有三种,而“因时间过迫不及致送贺仪者,有七十余号之多”。
“我想这里就很有问题可问。”刘平指出,“身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代总经理的杨敦甫最初为什么不愿惊动友朋?在他有意隐瞒之下,女儿的婚礼依然宾客纷至,这从另一个侧面又说明了什么?我想,从银行家自身,乃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身在业界的地位,以及其与实业界的关系角度考虑,其中确实传递出了某种暗示或解答。”
应文中某些关于婚礼细节的描述也颇值得一叙。既然地点放在以西菜闻名的“一品香”,仪式采用的自然也是新潮的西式风格。按照应文提供的名单,担任婚礼司仪的是怡和洋行机器部买办毛祝三,培成女校的教员郦秀珍奏琴(新娘多半便是培成女校的学生),天利洋行机器部买办程祥之和福新面粉公司经理华伟中出任介绍人,证婚人则是当年刚被纳税华人会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的著名金融家林康侯。“一方面,婚礼司仪、介绍人以及证婚人的身份,暗示了商业储蓄银行良好而亲密的银企关系与行业关系,另一方面,这个配置本身也是时期婚姻制度的现实反映。婚姻法规定,即便夫妻双方是自由恋爱采用西式婚仪的,在婚礼上依然需要配备介绍人,代表媒妁之言。父母双方首肯,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齐全,有按一定流程举行的、向宾客开放的结婚仪式,以及最终签署结婚证书,这是确认婚礼合法有效的几大要件。”刘平说。
新娘由父亲杨敦甫亲自扶入礼堂。大门与礼堂相距不过十余步,杨敦甫与女儿却步行了一刻钟之久。应俭甫因而在文章中调侃,“先生素性爽直,每以办事敏捷贵有精神训勉同人”,此时却“破格缓步,然严肃之精神并不因之稍减,亦可想见仪节之隆重矣”——第一手史料的好看也就体现在这里,区区“破格”二字,一个银行家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刘平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可资玩味的事例,是刊登在1948年8月《海光》十二卷八期上的《汉行崔经理与刘女士结婚记》。文章说的是64岁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武汉分行经理崔幼南与58岁的妻子在武昌珞珈山举行的一场“白头”婚礼。文章以生动的笔墨讲述了两人小说般传奇的,跨越三十多年时光的曲折恋情,读来分外有趣。不过真正引起我们关注的,却是这样一个细节:婚礼前日的6月30日,正值银行结账,崔幼南一直办公到深夜十二时,第二天上午,他“照常运动,照常到行签署结算报告,照常在行午餐”,至当天下午,方“不动声色”地一个人悄悄渡江,来到婚礼的举办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直到晚间同事们得到喜讯,才成群结队赴崔府道贺”。文章作者对崔先生这一“突击的家式的结婚举动”大加褒扬,认为他“不惊扰同事,不破费别人的节俭作风,正刻绘出其自重而自律的为人美德”。
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讲述,和他们讲述历史的方式角度,以及我们对他们的讲述的理解,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就像刘平强调的那样,我们讨论银行人的婚礼,其用意或许也并不仅仅在于追忆旧时“婚礼”,归根结底,是想透过一场婚礼的镜像,触摸到“银行人”的肉身,是要从史料描述的浓淡取舍中,读出同为银行人的写作者与被写者,读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交游、他们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我们的整个金融历史,正是由无数个这样的个体集合而成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武汉婚庆网
武汉婚庆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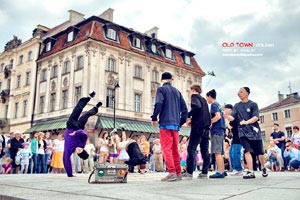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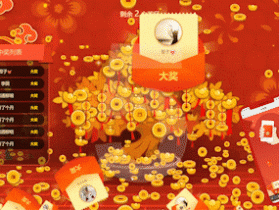




发表评论